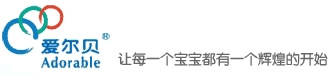爱尔贝会员中心

经典教育类电影介绍二:《放牛班的春天》
爱尔贝早教中心 时间:2012-7-29 http://www.adorable.com.cn/
《放牛班的春天》
——这个世界也许有卑微的人,但却没有卑微的情感
导演雅克·贝汉说:孩童时代的面孔,连同内心深处的情感对我们是如此珍贵,以至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中,幼年时期的记忆永远无法磨灭。
也许不会有人知道,在法国某个小镇的郊外,通过一条幽长而宁静的梧桐树围成的小道,坐落着这样一个充满暴力,恐怖,严历制度的少年管制学校。这里住着一群不学无术,冷漠,野蛮无知的孩子。他们是使家长无奈,老师烦恼的问题少年。谁也不会在意这些尚未成熟的心灵中所怀揣着的天真烂漫的梦想:将军,热气球飞行员,建筑家……刻板的校长只能用“犯事的人,必定受罚”的准则加以暴力来惩罚他们。原任班主任束手无策,无奈调职,然而一个公认为一事无成的马修来了,他在乐谱上写下了专门为孩子们谱写的歌曲,他用纯净的音乐唤回了管教们冰冷已久的心,解脱了束缚孩子们身心的绳索,抚平了他们受伤的心。就这样,放牛班的“小春天”在每个孩子的心田瑰丽而至。他们的梦想也逐渐开始萌发。
神圣而纯净的音乐不但净化了孩子们的心灵,更对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仁爱、友善、宽容的极致是让所有的观众眼中充满喜悦的泪水。
是的,是这样一个被世俗所公认的卑微的“失意的乐者,失业的教师”给“放牛班”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春意”。影片从顽皮的孩子那一庄一勰的嘻笑怒骂间折射出一颗身为教育者的马修的“善良、宽容、耐心”的心,他以跳动的音符驯服了一群如小野牛般的桀骜不逊的心灵,让他们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春天的气息……
被剧情所牵动的同时,也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些教育孩子的心理学知识…..
将这群问题少年集中强制关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一道道铁门禁锢着他们的心灵世界。从此只能看到高墙围着的四角的天空。感受不到爱和尊重,不许依恋;犯了事,只能用皮鞭和囚禁处理。尘封的心灵开始扭曲,在这里有以李基度为代表的攻击性强的儿童,他砸伤老麦;还有以皮比诺为代表的,由于失去双亲,缺少依恋而孤僻,甚至抑郁的儿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让单亲妈妈头痛,对音乐极有天赋,但又自尊心十足,相当敏感的莫朗。
对李基度和丹东这样攻击性强的孩子。马修并没把他们交给校长体罚。他派李基度来照料因他而致伤的老麦。让他自己体验生命的脆弱,以及自己冲动行为的后果。“他是一个害羞的孩子,像我一样害羞,他已经知道他错了。”老麦以这样慈爱和宽容的方式感化了李基度,当李甚度像所有犯了错的孩子那样看着远去的老麦时,惊恐地问马修:“他会死吗?”马修抚摩着他的头“不!医生会救他的,”用这样宽容的语气消除他内心的不安。
至于如丹东那样冥顽不化的少年,马修也极力挽回。当丹东受罚时,马图曾这样试图阻止“等一等,他是我唯一的低音!”……
与攻击性行为相反,对幼小就缺少依恋而产生抑郁,甚至略显自避的皮比诺而言,马修则是像父亲一样去关爱他。他从不谈自己的理想,不唱歌。但却出乎意料地被选为合唱团副团长。让他逐步感受到集体活动的快乐,和爱心的力量,从而使皮比诺摆脱了不幸的阴影。
全片的焦点人物就是最后成为音乐家的莫朗。他曾被上界班主任称为“天使的面孔与魔鬼的心灵”。他是由单亲妈妈抚养的。与别的孩子不同,他更有自尊心,更敏感。马修体会到这位单身母亲的含辛茹苦,这个孩子的任性。一方面极力以“补牙”为幌子,用善意的谎言在母亲面前维护莫朗的自尊心,而另一方面则冒着触犯校长的危险将正在受罚的莫朗放出去,探望母亲,对他也极为信任;发现他的独唱天赋,又积极培养。特别是莫朗将墨水瓶投向他时,他依旧宽容地安慰这位失望的母亲;另一方面以取消莫朗的独唱资格使他明白: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必须先尊重别人。特别是为伯爵夫人演出的那一天,马修从新给予莫朗充分肯定,最终感化了这头“小野牛”。
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都应该得到尊重,存在就是有价值的。马图在接受校长的任务时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不体罚学生;第二,让我来处罚犯事的学生;第三,不要透露他们的名子。这三条无一不体现了他对幼小心灵的人性关怀。
当马图听到淘气的孩子以嘲笑他的口气唱着那支“老秃头,老秃头……”时,马图并没生气,他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念念不忘那支歌,唱得差,但毕竟还是在唱歌”。于是,他运用音乐活动为主要手段,来调整孩子们的不良心理。每一个音符,宛如一个个鲜活的精灵,“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最终实现心灵的转向。如果儿童的记忆伴随情绪、情感过程,则记忆最为深刻;组织合唱团,是一个小活动,在活动和游戏中,孩子们心灵澄清,这种教育很注重体会,亲身体会已不再是简单的认知水平,而是带有情绪、情感过程,这样可以使孩子们留下最深刻的烙印。
怀着对已逝岁月的缅怀,聆听着如天籁般悠扬的歌声,当灵动的音符触动到心灵的深处,忽然想到美国的诗人爱默生曾说过:“这个世界最动听的是还未唱出来的歌。”是的,也许无论一个人卑微与否,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可以有美好的情感……

海面上的清风
托起轻盈的飞鹭
从白雪皑皑的大地飞来
冬日转瞬即逝的气息
远方你的回声飘离了
西班牙的城堡
在回旋的风中转向 展开你的翅膀
在灰色晨曦中
寻找通往彩虹的路
揭开春之序幕
海面上的清风
托起轻盈的飞鹭
停落孤岛的礁岩处
冬日转瞬即逝的气息
你的喘息终于远去了
融入群山深处
在回旋的风中转向 展开你的翅膀
在灰色的晨曦中
寻找通往彩虹的路
揭开春之序幕
哦 黑夜刚刚降临大地
你那神奇隐秘的宁静的魔力
簇拥着的影子多么温柔甜蜜
多么温柔是你歌颂希望的音乐寄语
多么伟大是你把一切化作欢梦的神力
哦,黑夜仍然笼罩大地
你那神奇隐秘的宁静的魔力
簇拥着的影子多么温柔甜蜜
难道它不比梦想更加美丽
难道它不比期望更值得希冀
4、风筝
空中飞舞的风筝
请你别停下
飞往大海
飘向高空
一个孩子在望着你呐
率性的旅行
醉人的回旋
纯真的爱啊
循着你的轨迹
飞翔
空中飞舞的风筝
请你别停下
飞过大海
飘向高空
一个孩子在望着你呐
在暴风雨中
你高扬着翅膀
别忘了回来
回到我身边
5、夏日的微曦
夏日的微曦
驿动的梦
我的心燃起
蓦地腾飞
远离大地
泪水已抹去
了无痕迹
我沉醉其中
一切在闪耀
风中的船帆
远方的海岸
这是夏天的时刻
歌颂自由的歌曲
乌云被抹去
夏天的初月
欢乐的震颤
一切在跳跃
一切变得明亮
荣辱恐惧抛诸脑后
孩子们的恐惧
悲伤的呓语
了无踪影
夏日的微曦
我的心燃起了
蓦地腾飞
远离大地
泪水已抹去
了无痕迹
我沉醉其中
一切在闪耀
.
总部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林和东路华庭路4号富力天河商务大厦810
电话:020-38814279 020-38814508
粤ICP备20055818号-1